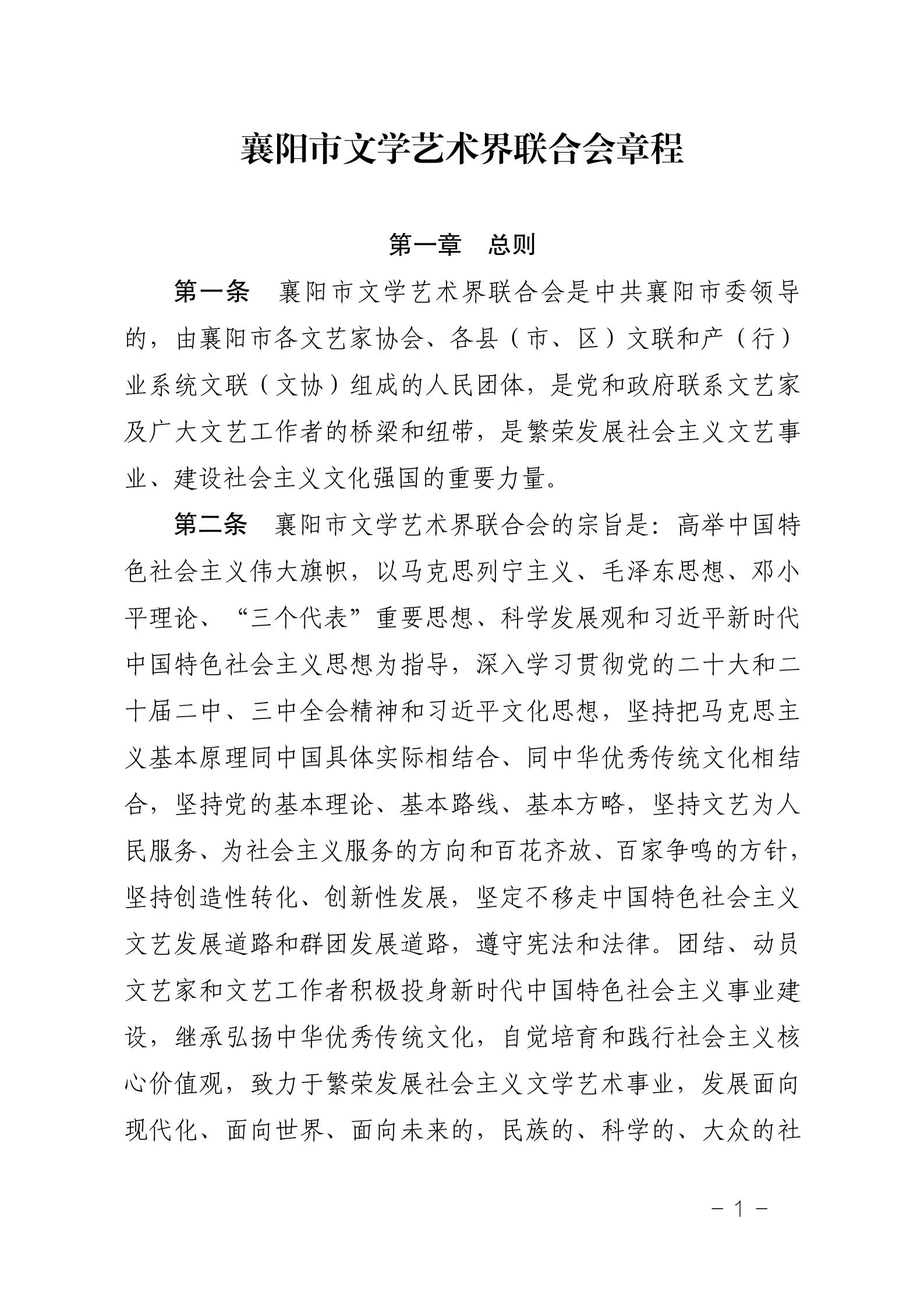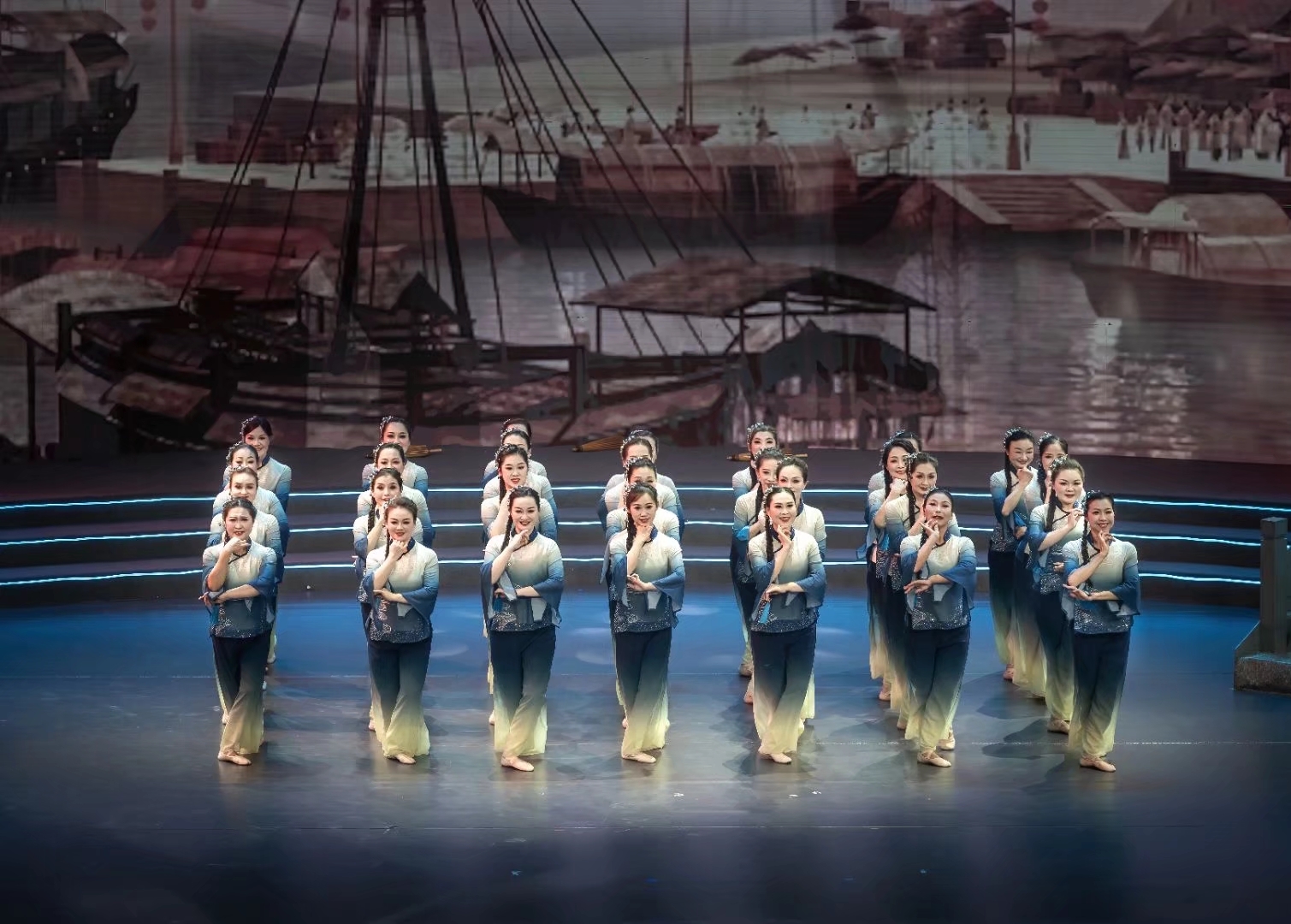一骑红尘越千年 “天下腰膂”看襄阳
这个夏天,一枚穿越千年的荔枝点燃了荧屏。当电视剧、电影《长安的荔枝》中的驿马踏起红尘,岭南的鲜果疾驰向长安时,无数观众为唐代“快递员”李善德的生死时速而屏息凝神。剧中李善德规划的四条荔枝运输路线中,有三条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古城襄阳。
“在任何一个朝代,襄阳都是一座无法绕开的城市,我的作品《长安的荔枝》中最优运输路线必经襄阳。”2023年,《长安的荔枝》原著作者马伯庸在襄阳读者见面会上的发言,也道出了襄阳这座“天下腰膂”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七省通衢——“最优路线必经襄阳”
“长安的荔枝运输线,襄阳为何成为必选项?”近日,《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的运输路线图引发了全网热议。
剧中,“荔枝使”李善德铺开地图,汉江中游的襄州(今襄阳)成为关键节点,四条备选路线中,有三条必经襄州。经过反复测算,李善德最终选定的路线全长2800公里,即:走梅关道至吉州,转西北到潭州后换水路,经汨罗江入洞庭湖,横渡长江沿汉江至襄州,再经襄河、丹河到商州,最后下舟乘马,沿商州道入关中,走蓝田至长安。
这条“最优路线”并非艺术虚构。襄阳自古便是交通要塞,荆襄古道与随枣走廊在此交会,构筑起贯通南北、连接水陆的枢纽。剧中路线的设定,正是襄阳“南船北马”历史地位的生动写照。这座雄踞于汉江中游、南阳盆地南端的古城,北接中原、南连江汉平原、西通巴蜀、东达江淮,自古就有“七省通衢”“天下腰膂”之称。
“岭南荔枝北运,走长江入汉水最为便捷,而襄阳正是汉水与南北陆路的交会点。”襄阳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计划科科长李玲解释,在古代,汉江是重要的水运通道,在此换乘,既能借水运减少颠簸损耗,又可经陆路快速接入关中商道,满足速度与保鲜的双重需求。
此外,诗圣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名句,以及刘禹锡“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等描绘,也是对襄阳“南船北马”盛景与唐代交通要冲地位的生动注脚。
诗证驿路——襄阳进士的荔枝史诗
荔枝道的存在,还在一位襄阳籍进士的诗句中找到了历史的回响。
贵妃吃的荔枝来自巴蜀还是岭南,是荔枝道学术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随着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的播出,杨贵妃所食的鲜荔枝究竟来自何处,再次引发了广泛热议。
清代吴应逵《岭南荔枝谱》引《徐氏笔精》记载:“唐鲍防,襄州人,天宝末举进士。时明皇诏马递南海荔枝,七日七夜达京师。防作杂感诗云:‘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皆从林邑山。’”
这首珍贵的诗篇,成为《长安的荔枝》中引用史料的核心支点,也是“岭南说”的重要支撑。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徐俪成在《长安荔枝的历史真相与文学书写》中指出,史学家们对玄宗朝长安荔枝来源的研究,其中引用的唐代史料基本是文学作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杜甫的《解闷》《病橘》,以及曾经历过天宝时期的中唐诗人鲍防的《杂感》。
马伯庸在《长安的荔枝》后记中也坦言:“关于岭南荔枝道的路线,我是用鲍防的《杂感》和清代吴应逵《岭南荔枝谱》里提供的路线作参考,综合卫星地图研判而成。”
一首襄阳古诗,就这样串联起千年时空。
驿路新生——从红尘一骑到万家通途
然而,荧屏上疾驰的驿马背后,是沉重的民生代价。
“人马驰毙只为红颜一笑?”剧中李善德亲眼目睹驿站骏马累毙的场景,揭开了盛世华袍下的累累创口。杜甫的“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以及欧阳修的“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之句,皆是对权力任性的警世与控诉。宋代曾巩进贡荔枝干果时的忐忑,与清代学者何焯“恐启君王奢念”的洞见,无不映射着对“一骑红尘妃子笑”背后民生疾苦的深刻反思。
马伯庸的创作深意正在于此:那个时代的“快递小哥”,如何在万里之遥与落后的保鲜条件下,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他希望借古喻今,让享受便捷的现代人,看到当下无数“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的付出与努力。
而今,襄阳这座已承载了千年“天下腰膂”地位的古城正经历着一场华丽蝶变:汉十、郑渝高铁在此交会,福银、二广高速构筑“黄金十字”,124家A级物流企业集聚于此,织就了一幅水、陆、空联运的现代运输网络图景。
从贡荔疾驰的驿站,到辐射全国的物流枢纽;从贡荔保鲜之忧,到冷链仓的精准温控——变的是日新月异的工具与效率,不变的是襄阳贯通南北的枢纽地位与使命。
从荔枝驿站到国家枢纽,襄阳的交通地位千年未变。如今,它承载的已非仅供一人一笑的荔枝,而是驶向千家万户幸福生活的时代愿景,也是交通服务民生的本质回归。(全媒体记者 张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