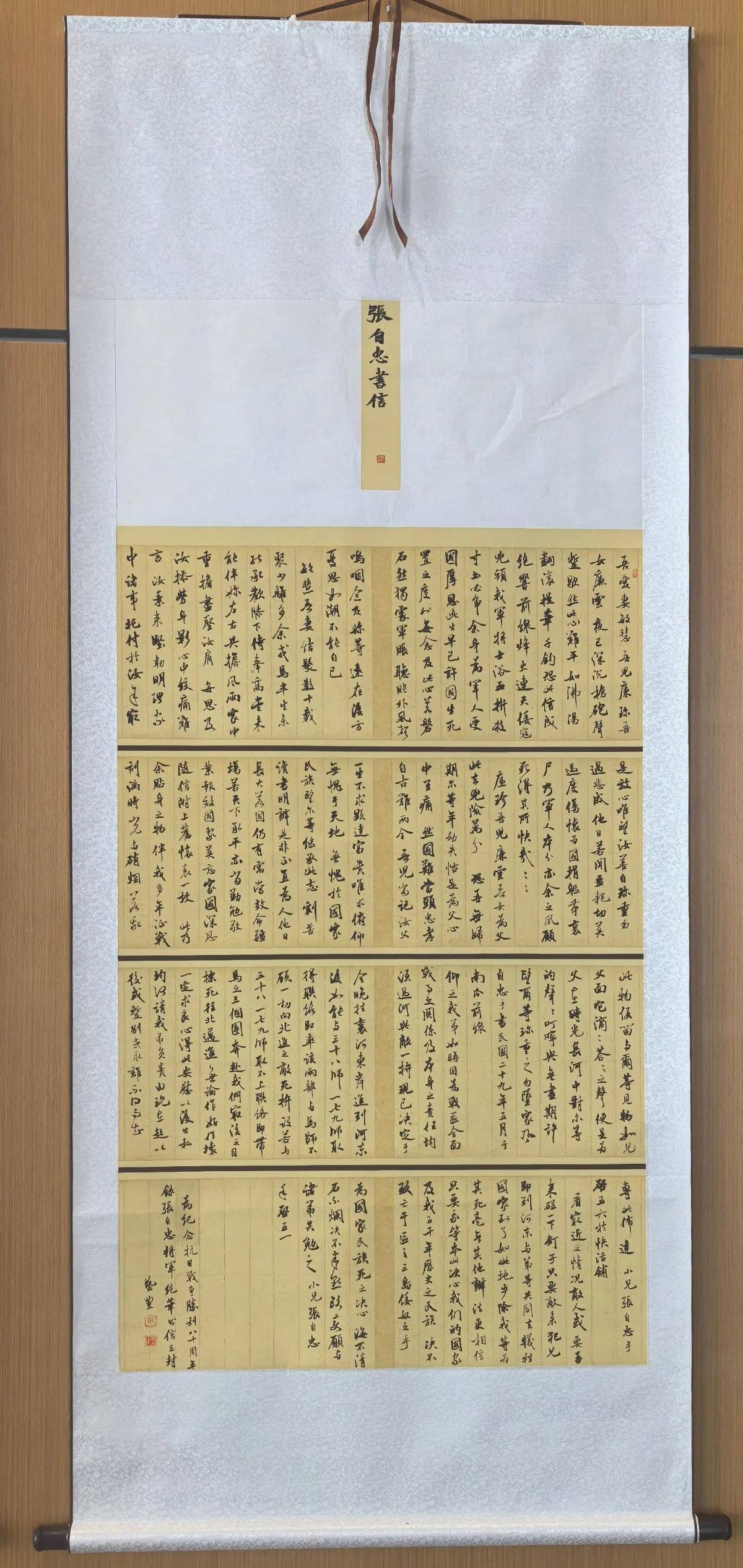【文学评论推荐】古典叙事与传统文化交织下的历史女性书写
古典叙事与传统文化交织下的历史女性书写
——评艾子《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
(刘永恒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襄阳作家艾子的长篇小说《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于2023年发表,全书共31万字,时间跨度长达35年,地域跨度涉及襄州、抚州、汴京等地。小说以北宋女词人魏玩的命运为主线,围绕其流传下来的13首诗词进行巧妙构思,讲述了魏玩与丈夫曾布由相识、结合、深爱到疏远的爱恨情殇,以及她由一位普通诗词爱好者成长为“大宋第一女词人”的艰辛历程。魏玩作为打破“男子作闺音”词坛局面的第一位女词人,是北宋作词最多的女性,也是宋代女性词人中社会地位最高的一位。但目前在知网上以魏玩为对象的研究论文仅有7篇,相比于李清照、朱淑真等人千百余篇的研究论文,魏玩的研究现状与其重要地位极不相称,魏玩的诗词艺术和历史价值仍有待于发掘和弘扬。如此看来,书写这位北宋女词人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艾子的《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正是为发掘襄阳历史人物,传播魏玩诗词文化,为北宋女词人魏玩正名迈出的重要一步。
《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以北宋女词人魏玩为创作原型,魏玩的生平事迹为创作脉络,结合作者的想象进行创造性书写,构成历史与虚构的交织,显然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提到历史小说,我们首先会想到熊召政的《张居正》、唐浩明的《曾国藩》、姚雪垠的《李自成》,这些历史小说多是男性作家书写男性人物,而艾子写作的《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正是弥补了当下历史小说中女性主人公稀缺的局面。并且,作为女性作家的艾子与同样身为女性打破“男子作闺音”的魏玩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创作需基于真实历史,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需于史有据,但毕竟是文学创作,允许而且必须进行审美创造,否则就与史书无异,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历史学家的画面要力求真实。小说家只有单纯的一项任务:要构造一幅一贯的画面、一幅有意义的画面”[],《暗夜中的怒放》便是这样一部基于历史真实同时兼顾审美艺术的小说。小说在书写北宋女词人魏玩的同时,侧面描绘了北宋时期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之争等历史细节。除还原历史事件之外,与魏玩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在小说中均有不同程度地展现,如米芾、苏轼、王安石、沈括等大量历史人物也在小说中接连登场。在基于历史事实创作的同时,作者根据魏玩主要生平事迹对其人物活动进行创造性的想象虚构,如魏玩初嫁抚州与丈夫曾布乘船赏荷、种桑养蚕补贴家用、与金兰汇众姐妹饮酒作诗、书肆失火词稿尽毁等等,这些情节对丰满人物形象,刻画人物真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具审美意味。
一、古典叙事:文学作品的表与里
在叙事策略上,小说继承了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如“草蛇灰线”的叙事技巧和“说书人”的叙事方式。关于古典叙事,董乃斌曾说过:在形形色色的文学叙事之中,存在着某些频繁呈现,甚至代代传承的表现特点,这些相对稳定的特征贯穿于整个文学史。[]“草蛇灰线”最早作为文法使用出自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指的是:“中国特有的印象式批评的一种体现,是用草中之蛇的变化不定,和手抓灰烬画线的时有时无来比喻,着眼于层次与层次或段落与段落的为文章法。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作者常有意识地对物件、状态、时间、细节作形式的反复以此来充当某一情节的贯穿线,但每一种重复都表征着内涵的差别,言说着情节的发展。”[]如小说第四章,魏玩陪朱夫人到南台寺还愿时,突然听到几声女人的惨叫,而这几声惨叫在后文中也得以证实正是昔日好友莹莹。此外,在第二十二章,原本不信宗教佛道的魏玩在经历了刘快活用酒和丹药医好丈夫之后对道教增添了几分相信,以及宝婵向魏玩建议去三圣庵听净颜师太讲法,这些微小情节都为后文魏玩无意间进入三圣庵与净颜师太(也就是昔日好友莹莹)重逢埋下了伏笔。除此之外,作者在第十一章以闲叙之笔描写了一个青色幞头、灰色直裰的圆脸中年男人,而这男人正是苏轼,作者通过这样一个不起眼且将苏轼“陌生化”的描述,为后文第二十二章苏轼对魏玩所说两人十几年前有一面之缘埋下伏笔,不仅令魏玩诧异,同时使小说面前的读者也深感惊奇,由此可见作者心思细腻,为情节的设计极费心力。同样在第十六章中,芳树对丈夫愚顺的自白也为后文第十九章的芳树因不能生育而自杀的悲剧埋下伏笔。诸如上述种种现象,正是作者对于“草蛇灰线”这一传统叙事技巧熟练运用的体现。
除“草蛇灰线”外,小说还采用了“说书人”的叙事方式,“说书人”是从宋元时期模拟书场中的说书人对听众讲故事演变而来的叙事方式。“说书人”以全知视角讲述故事,具有极强地控制故事的能力。“说书人”不但通晓人物的心思、梦幻,而且预知因果,出入神鬼世界,是一个上帝般的叙述者。[]小说中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随处可见,如“这是北宋嘉祐元年六月初二的清早”“当时属于天下十八路之一的京西路”“今日租船的不是普通人”[],“熙宁七年,变法已经六年了,朝中局势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大宋制度,官员的官阶到了哪个品级,或对朝廷有特殊贡献,便要对其母亲和妻子封赠”[],“你道来者是谁”[],以及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且说”“却说”作为开场引入词,上述种种迹象表明作者采用“说书人”的叙事方式。通过回归传统叙事,以此弥补现代小说中的叙事缺陷,使得作者进入文本,与读者进行叙事交流,拉近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令读者产生亲切之感,将故事叙述得有温度。
总之,小说在叙事策略上继承了古典小说中的草蛇灰线的叙事技巧和说书人的叙事方式,从而以古典叙事的方式构成小说的表与里。
二、诗词服饰:传统文化的隐与显
在内容呈现上,小说巧妙地将魏玩的诗词创作与故事情节进行结合,在向读者展示魏玩人生经历的同时书写魏玩每首诗词创作的背景和心境,其间有许多作者借魏玩之口对所作词曲的解读阐释,因此这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部魏玩诗词鉴赏。魏玩作为北宋第一位女词人,在书写魏玩的同时如果脱离魏玩的诗词创作显然无法将魏玩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生经历得到完整细致地刻画展现。小说在描绘魏玩人物心理活动时往往伴随诗词创作,从而描绘人物的形象、展现场景的氛围,正如《红楼梦》中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判词,增强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同时,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情感表达提供支撑和暗示,并且能够为读者带来更加深刻的情感体验。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词人借助诗词体裁进行表达的隐性方式。艾子在小说创作中巧妙地融入魏玩诗词,显然是希望借助小说的文学形式将魏玩诗词的文学内涵和艺术价值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穿透诗词与小说体裁的壁垒,全面充分地展现在读者与世人面前,揭开历史覆盖在魏玩及其诗词上的沉重面纱。
除诗词创作与小说故事的巧妙结合之外,小说中繁复的服饰描写也尤为值得关注。相比于诗词的隐性呈现方式,小说还描绘了大量具有显性特征的传统服饰。小说中存在大量服饰描写,如“葛金色丝质长衫”“月白色撒花烟罗衫”“玉色绣折枝堆花裙”“湖蓝色缠枝纹罗裙”“石榴红緙金丝云锦扣身袄”“墨绿色双绣绸衣”等等,与《红楼梦》中的“翡翠撒花洋绉裙”“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簇新藕合纱衫”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色彩缤纷、样式繁多的服饰描写,对小说叙事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通过描绘不同样式的衣服,如“衫”“裙”“袄”暗示着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化。第二,通过服饰颜色描绘体现人物性格,如抚州贺员外礼诚到曾家拜访所穿“葛金色丝质长衫”,其衣服颜色“葛金色”便尤能凸显贺员外趋炎附势的人物性格。第三,服饰有着明确的社会性,透过服饰,可以破译对方穿着上所隐寓着的社会密码。[]如曾布在中举为官之前,穿着仅是“一顶崭新的玉色幞头,一件灰色长身直裰,一条深色丝绦带”[],而在做官发达之后,“头戴顶精致的黑纱幞头,穿了件紫色暗山水图案的棉公服,腰间挂了一个金鱼袋”[],曾布的服饰华丽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其身份地位的提升通过前后服饰的巨大变化也得以显现。除上述人物众多、服饰华丽的描写之外,小说还描绘了众多风俗传统,如襄州的“穿天节”,还有宋代盛行的“挑菜节”,以及汴京城在元宵节赏灯游玩的繁华景象,营造了一种别致生动的文化景观。
综上,小说在内容层面展现了古典诗词、传统服饰以及风俗节日,从而实现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隐性表达与显性呈现。
三、女性意识:身份的焦虑与认同
小说在目录部分以各个事件为名进行章节划分,从中可以看到魏玩完整的一生以及人生中各个重要的事件阶段,展现出一条清晰的魏玩人生脉络。在这部小说中,涉及人物众多,仅魏玩与曾布的直系亲属便有十余位,加上众多好友仆从,人物更是多达六十余人,如何处理好众多人物的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作者在小说目录之前特地列出了一份人物表,对读者理清人物关系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增强了小说的阅读体验,缓解了因人物众多而带来的阅读障碍。在描写人物时,作者并没有采用雨露均沾的写作手法,而是主次分明,对主要人物大量着墨,次要人物仅是简单描述,因此虽然人物众多,但作者并没有偏离写作的中心,始终围绕魏玩进行叙述。作为小说主人公的魏玩,其人物形象可谓是生动且真实的,从初为人妇到受封为“鲁国夫人”,魏玩为人始终真诚勤恳,丈夫常年在外,总能体贴理解丈夫,虽然留她一人独守空房,却能将偌大的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想尽办法为家庭补贴家用。但是魏玩也是不幸的,丈夫不在身旁的日子,魏玩受尽了相思之苦,短暂的青春年华却只能独自为伴,如小说中魏玩半夜赏梅,“魏玩看到此景,心中一动,觉得这梅花和自己好有一比。它纤巧独立的风姿,无人欣赏;小小的琼苞中藏了多少幽香,也无人知晓”[],与小说题目遥相呼应,魏玩的人生便是“暗夜中的怒放”,无人可知,无处可说,满腹忧愁只能诉诸词作。又如魏玩面对长丰洲的郁郁芦苇和滔滔江水所发出的人生感慨:“如此想来,这世间万物,骨子里,俱刻着‘悲苦’和‘迅忽’两词了。[]”“悲苦”和“迅忽”这两个词便是对魏玩人生一世最为真实而又生动的概述。此外,还应注意到,小说中作者借魏玩之口反思女性在历史长河中的频繁缺席现象,“历史上,青史留名以男人为主,妇人寥若晨星,本朝怕也概莫能外”,“这个世道,妇人想要留名,非得有卓越的英才不可”[],魏玩以专心作词的决心对男性书写下的女性塑造表示坚决反抗。
面对丈夫曾布常年不能相伴的凄惨现实,随之为魏玩带来身份的焦虑。魏玩的首要身份便是曾布的妻子,然而妻子的身份在两人终年不得相见的现实下也仅是有名无实,使得魏玩产生身世孤苦之感。但魏玩始终坚持履行妻子义务,以忠贞诚恳、勤俭持家的美好品行构建自我身份认同。还应注意到,在曾布妻子的身份之外,魏玩更是一位女性词人。面对万般愁苦的生活现实,魏玩只得借助诗词创作抒发自己的胸臆,但众多诗词因书肆失火只得尽数毁坏,作者这一情节安排既为历史真相进行了合理解释,又对魏玩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更为饱满细腻的刻画。面对接连遭遇的悲惨现实,魏玩并没有放弃词人的身份定位,而是在振作精神后继续创作诗词。与此同时,身为词人的魏玩回望诗词创作的历史长河,意识到在过往的诗词创作中,男性词人占据了词人群体,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男子作闺音”这一不合常理的诗词创作现象。正如刘俐俐所说,在巨大变故中个体的处境有所改变时,这种潜隐的意识往往伴随着失落或者痛苦的复杂情绪表达出来。[]面对诗词创作中女性缺席和失声的现象,魏玩的女性意识也在寻求词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进而投射到魏玩的诗词创作当中,通过诗词抒发女性词人的创作志向和闺怨之情。
与女性意识萌发的魏玩相反,小说中的另一女性人物芳树却是古代封建制度下的悲剧产物。在她身上表现出了古代女子的真实写照,面对丈夫品行不端,甚至家暴的情况下,仍固执地认为“顺夫为贤”,在这样愚忠的错误观念下,最终导致了她自杀的悲剧,而这悲剧的造成,并不能简单归咎于芳树自身的错误观念,更应看到这是在封建传统束缚下寻求传统女性身份认同的结果。
是以,作者通过书写魏玩面对身份焦虑进而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展现出北宋女词人魏玩的女性自强意识,进而映射出魏玩不屈的人生态度和坚定的诗词创作决心。
结语
艾子的长篇历史小说《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通过古典叙事描绘了北宋女词人魏玩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且将传统文化融汇于小说创作之中,同时刻画出魏玩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所萌发出的女性意识。但作为艾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难免在创作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小说的叙事节奏较为平缓,情节冲突时缺乏人物心理的深入描写,并且人物与所处时代的结合不够紧密。但瑕不掩瑜,《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语言展现了艾子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发掘襄阳历史人物的赤诚真心和创作天赋,对于打造与弘扬襄阳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通过这部小说可以揭开历史覆盖在魏玩及其诗词上的沉重面纱,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襄阳除了诸葛亮、孟浩然、米芾等人之外,还有一位伟大的北宋女词人魏玩。